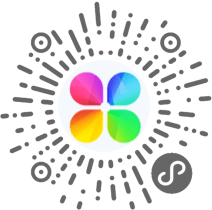【一位抑郁症患者的自白】左脑沮丧,右脑冥想
9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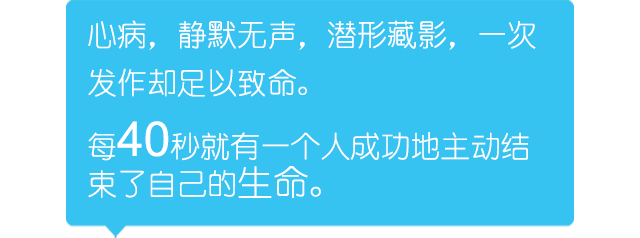
我的大脑病了,我心知肚明。
焦虑迟徊不去,低落如影随形。心悸,胸闷,睡眠不足导致头痛,胃部的感受在脑中具现化成一幅溃疡图。黑咖啡一杯接一杯,而工作效率仍然低下。几个月来,邮箱里的未读邮件数跳到三位数。我不回信,不回电,不看短信与微信,中断了刚开始执行的锻炼计划,尽可能回避与亲友的社交聚会。在凌晨的熹光中,我从应考梦里疲惫万分地醒来,却没有动弹甚至睁眼的力气。只祈盼床铺化为流沙,可以将我慢慢吞没,不留一丝痕迹。
如果 “慢性拖延症”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乃至身心,那么或许你罹患的不止是拖延症。
“一切都离我而去,唯有对你善良的确信仍存。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人生。”这是伍尔芙留给丈夫的遗书。每个所爱仍在的抑郁者想必会心有戚戚。考虑到目前我的生存对我所爱者或仍利多于弊,我尚未拟定详细的自尽计划,只在心底隐秘地期望自己能忽然变成一种 “不存在”的状态。倘若有办法能把我曾存在的痕迹从那些爱我的人脑中抹得一干二净,我会毫不犹豫地使用,然后开始囤积那些理论上不难到手的药片,在某一天仰脖“顿服”——此术语意为一次全部服下。
心病如同心脏病,静默无声,潜形藏影,一次发作却足以致命。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40秒就有一个人成功地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庄雅婷写,一想到人生如何走到这一步,水就从脚下涨了起来。在我身遭,水位不断上涨。我需踮脚抬头,方能艰拙呼吸。
算过自己抑郁症状自评量表(SCL-90),自动思维问卷(ATQ)和功能失调性态度量表(DAS)的得分,我终于去了最近一家三甲医院的心理门诊。带着疑似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诊断,以及七片盐酸帕罗西汀出门,我发了条信息给前不久刚听我告解过情绪问题的猛犸,说计划开始吃抗抑郁药。
他问,你试过其他办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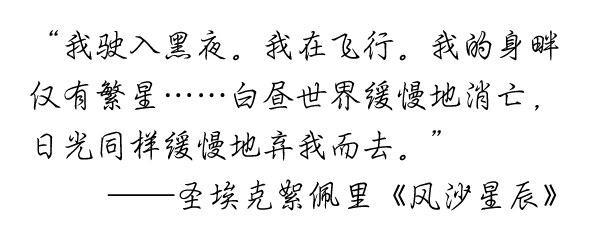
都知基本五味是酸甜苦咸鲜,但学界对基本情绪的划分可没那么一致,一种分法是四大类:愤怒、恐惧、悲伤和欢乐,有人还加上惊讶与厌恶——不论怎样分,总是苦多于乐。这些情绪的产生和表达方式源自本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表达同样情绪时仍做出类似的表情。
而情绪障碍一点不罕见。当遭遇所爱逝去、健康滑坡、工作受挫、添丁进口(每个亲妈都曾想把孩子掷出窗外)……要保持心境喜乐实在有点勉强。还有些激素、降压药、镇静剂、抗菌抗病毒等药物的副作用就包括使人抑郁。五分之一的人曾变得非常低落。而每二十人中就有一个始终处于抑郁之中。至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95年凯斯勒等人在研究里报告,10.4%的女性在她一生中会与PTSD狭路相逢,另有5%的男性终不能幸免。
从年龄来说,比起老年人,青壮年更易抑郁。从职业来说,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常生“心病”。从大五人格维度来说,愈是神经质,就愈容易产生心理困扰。从大脑来说,右侧前额叶皮层活动强于左侧的人,对负面刺激反应更灵敏(还想付天价“开发右脑”吗?)。从基因来说,携带变异G1463A,或是拥有5-羟色胺转运蛋白(5-HTT)基因里效率较低的“短版本”的人,在压力挫折接踵而来时确实会处于不利境地。从特殊能力来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比普通对照组在创造力测试上得分高出一半,而情绪紊乱的艺术家名单可以列成一条星光大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全体药不能停,也不意味着躁狂抑郁焦虑可以帮你转职成创作者。这只说明,病程迁延的抑郁症确实不能简单地用“贱人就是矫情”来概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全线紊乱,血清素、谷氨酸和5-羟色胺一路走低,皮质醇和去甲肾上腺素则步步高升。警戒的杏仁核时刻活跃,而记忆的海马区日渐萎缩……这些生理变化可以解释为何我常觉疲惫又易怒,为何又总处在一种“战或逃”的纠结状态中。
抑郁又不单只是一系列化学分子的变化。
研究者早就发现,抗抑郁药能即刻提升体内“快乐分子”的水平,却不能同样立竿见影地提升情绪。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往往要至少持续吃上两周,服用者才会从萎靡转向振奋。一种解释是大脑中要形成“正向回路”,需要长出新的神经元,或需要旧神经元长出新突触,故此耗时。另一种可能是,有时药物对情绪不起作用,是因为大脑里正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自尊毁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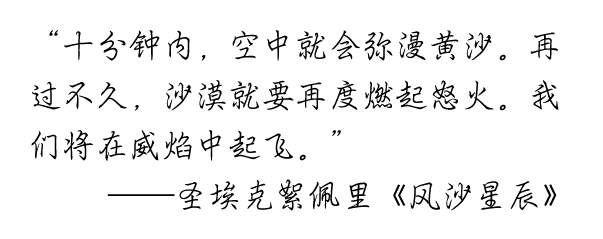
半个世纪前,心理学家埃利斯(ElliS)建立了情绪的ABC模型,A代表外界情境,C代表情绪后果,而B则是我们对情境A的解读——这种解读往往一闪而过,快得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更没有意识到,其实并不是外界情境A,而是我们的解读B,真正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情绪反弹C。我们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刺激,决定了我们应对的方式。而要改变情绪以及反应,首先得改的就是解读方式,停止用那些超出自身控制的事件来评价自己。事固有不遂,我却不曾改。
猛犸给我留言:当我们把事情的起源归结于个人的、永久的、广泛的因素时,我们就会沮丧不已。当我们采取相反的解释方式,我们就会动力十足。
然而,我们是多么喜欢戴上有色眼镜,急切地对面前的事物下一个判断,为自己的遭遇创作一个因果俱全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无论多么错误扭曲——随即成为我们所有判断的出发点。
在负疚感如潮水般淹没我的时刻,我对自己的评价也降到了谷底——我令人失望,我令自己失望。我的生活一塌糊涂。没有人理解我。我到底在做什么……类似的“自动思维录音带”在我脑中反复播放。嘘,请屏息,切莫呼救,此人已无可救药,何必浪费他人宝贵时间?
丫米问,有段时间总担忧若与朋友倾吐困扰,朋友会不胜其烦。但换个角度想,朋友向自己诉苦时,自己可以耐心倾听,为什么轮到自己身上就认定朋友会不耐?“难道世上只剩我一个善良的人了吗?”
心理学家舒尔勒说:“在大脑里,我们给出打败自己的评价。”诚哉斯言。当我无休止地思考自己的哪些“错”导致了如今的困境,我就成功建立了所谓的“负性思维模式”——不是说自省不重要,但倘若每“自省”而况愈下,千万当心。而我也发现,每次(被违诺的负疚感压倒而)不得不与亲友聚会后,哪怕一直忙于假扮天下太平,未曾倾吐自己的困扰,但聚会结束后自己的情绪都会有所提升,或许是因为社交是个可以转移注意力,让脑中喋喋不休的“自我评价”稍微停止的时段。
另一选项是运动。运动对大脑的好处毋庸置疑——经常在转轮上跑的老鼠海马神经元会增加,认知测试里也能拿更高分。运动,尤其是会让你出汗气喘的有氧运动,能提升大脑的血流氧运和营养因子,能挽留轻轻地走正如它们轻轻地来的海马区新生神经元,能最终令多任务处理能力上升。对老者而言,即便以沙发土豆之姿颓然度过了此前的全部人生,从现在开始每日步行20分钟,一样能制造保质期三天的快乐分子内啡肽,让情绪为之一振。
然而,哪怕理智上知道阳光和有氧运动可以带来大改善,如运动时听个古典乐效果更佳。但当你忙于自责与修补破碎的工作生活,聚会也好,运动也罢,或是专心致志地享受一顿美食……这些能给我们“充电”的事,往往都因为“优先级不高”被取消或推迟(如今方信,磨刀不误砍柴工)。在最黑暗的时刻,下床、洗漱、换衣、套上跑鞋、出门跑上一圈去面对这个世界……臣妾做不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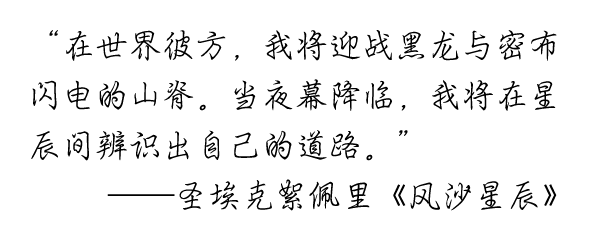
“你还没看我推荐的《改善情绪的正念疗法》?”
在拿到书一个月后,我向猛犸承认,我尚未翻开书页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它不能解决我此刻最紧急的问题(我正逼着自己学各种GTD方法以及读项目管理书呢);二是,这个书名看上去似乎不太“科学”(又一次地,我们是多么喜欢戴上有色眼镜,急切地对面前的事物下一个判断)。要是我先看到同一群作者写的《抑郁症的内观认知疗法》,说不定早就开始读了——这是后话。
著名的拖延症公式说,U=EV/ID。任务完成的程度U,等于对成功的信心(E)乘以对任务的愉悦度(V),除以你的分心程度(I),再除以多久能得到回报(D)。当EV都在低谷,而I冲到峰值,连番茄工作法都不再百试百灵。
那天我带着帕罗西汀回家,终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翻开了书。而最大的收获或许是,我不再将自己的大脑视为一个困于笨拙肉身内的“超我”,我将它视为一个重约两斤半的“小孩”,如果你希望大脑让你好过,别忘了这个小孩时时需要照看、安抚与哄劝。
这个小孩喜欢新鲜,容易分心,热爱刷微博刷邮箱频率如分娩产妇按镇痛泵。身体的姿态与动作可以影响这个小孩,体操运动员的结束动作——站直抬头挺胸,双手高举展开,保持几秒钟,就可以让这个小孩更为自信。这个小孩会哓哓不休地与我说它对世界的解读,(乔恩·卡巴金说,“平常思绪如震耳欲聋的瀑布,从我们的大脑湍激而过。”)那些解读并不一定符合真相,但会触发我的一些负面情绪以及“自动思维”(譬如,“我真是糟透了”,“我做什么都做不好”……)。而所谓冥想与内观,实际上是训练自己在负面情绪浮现时,在自动思维闪过时,能辨认出它们的存在,然后不批评,不抗拒,(心理学小实验,未来三十秒内,千万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只专注于把注意力拉回到正做的事情。
从集中营里生还的心理学家弗兰克曾说,在刺激和回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有自由,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回应。
而不论冥想、正念还是内观,在我看来,都是在训练自己扩大这个空间。若你能注意到自己的情绪,能冷静评估当下的情境,能游刃有余地选择回应,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既定模式战或逃。如此,在抑郁情绪可能卷土重来的转折点,就能给自己以及时的关注和干预,辨认出充满无尽思虑与消极想法的心理状态,并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冥想是追寻感受。正念是存在方式。是全神贯注地喝一杯咖啡。是深呼吸,是正常呼吸,感受气流的进出,感受胸腹的起伏。关掉随时随地监控“我现在的状态与我期望的理想状态距离有多远”的“行动模式”。开启“就在此时,就在此刻”的“存在”模式——当我开始留意树上的蝉鸣,在耳畔拂过的潮湿海风,许多美好的事物,只有带着好奇心去关注,它们的存在才真正在我的世界里凸显出来。
而卡巴金这么定义内观:此时此刻,带着目的去温和地关注,同时不加以任何评判。记住,我瞬间的想法并不等于我自己,更不等于事实。而不论大脑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论此刻的感觉是何等糟糕,始终把它们看作一次体验的机会——心跳加速,呼吸浅快?那是我的“战或逃本能”。胃部缩成一个灰色的小拳头?那是我的内疚加焦虑。血液直冲头部,额角隐隐作痛?那是我的愤怒与压抑。不论如何,呼吸,再呼吸,“事已至此,不如接受。原谅自己,顺便感受一下”。
如今冥想简直成了万灵药,它的身影在各种研究里闪现——抑郁焦虑,疼痛治疗,免疫调节,失眠哮喘,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甚至艾滋病……不是非得花上千美元去上五天内观认知课才能掌握这些技能。找个舒适的姿势,或坐或站或躺,然后接受此后发生的任何事情,睡着也好,不能聚精会神也好,毫无感觉也好,觉知此刻的体验。倘若想法游弋了,就简单地注意到,然后拉回来。冥想和内观在我看来,没有所谓“做对”,只有“坚持做”,几十亿次地坚持。
就在2007年,研究者评估了内观认知疗法的有效性,认为内观认知疗法对那些至少犯过三次的慢性抑郁症患者似乎显示出了一些阳性效果,当然,这种效果也完全可能归功于同时使用的其他哪种疗法(不管怎样,不要放弃治疗)。
至于我自己,完全痊愈了吗?当然还没有,我冥想时总会想起一个说冥想可促进脑神经元放电节奏趋向同步的研究,然后开始走神想象千亿个脑细胞同步闪烁,犹如一片璀璨壮丽的星空。我还始终把药片放在随身包里,风浪起时,那里会是最后的安全港。只是Chumbawamba唱,“我被击倒,但我又爬了起来,你无法永远打倒我。”夜色深沉,而我计划吃着火锅,唱着这首歌。